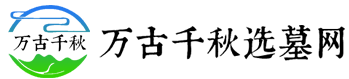200年来,万寿寺始终与长春市相依为伴,相向而行。红尘内外,各行其事,僧俗两界,和谐相处。然而,文革期间,万寿寺难逃厄运,毁于一旦。佛教僧众和信教群众无不痛心疾首。而企盼万寿寺能早日重建,祈盼佛光普照世间的善良心愿一直在人们的心中未曾熄灭。普度众生之愿,感悟众生之望,早在十年前,照睿就发心恢复古刹万寿寺,他四处奔走,多方努力,不辞辛苦,几经磨难。经过三年的栉风沐雨,2007年万寿寺开始在新址复建。他的善心善行终于修成正果。经过七年精心而又紧张的建设,2014年全新的万寿寺终于竣工面世。
唐朝开元年间,长春地区成为“安北都护府”的一部分。被中原人士称为“书山府”。当时,长春是拥有人口近10万的大城市,城墙面积扩大了数十倍。也因为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广泛传入东北亚地区,此后千年,一直影响东北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。
公元846年,粟末靺鞨领袖大祚荣在此建立臣渤海郡国,改“书山府”为“隆州府”定为国都。后迁都“敖东城”,但隆州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,人口已近50多万。
公元916年,契丹建国。长春地区成为管制重地,后因有一位王子在此地出生,遂将“隆州府”改成以王子名字命名的“耶律德光城”。
其后,女真族崛起,建立大金国,将长春改回祖先的“隆州白龙府”,迁都中都(北京)后,改称隆州“宽城府”(宽城子)。此时,人口近百万,城市已具备规模。
后来蒙古日益强大,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克宽城子。并下令拆毁城墙,将百姓迁移到辽阳和中原等地,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,只有在今天“小城子村”附近留下一点残存的遗迹。
明朝后期,女真再次兴盛,建立大清国。长白山成为满洲族(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)祭祖的圣地。古南部伊通河畔的驿站成为去长白山的必经之路。乾隆几次到长白山祭祖路过时,发现这里的气候比盛京凉爽很多,而且风景宜人,便说出“长白千载古喜州,春光无限在宽城”的诗句。
以上就是关于“长春”这一名字的历史由来。
夜幕已降。
元宝、巴图鲁一餐饭用完,便各自回房,一夜无话。
……
第二天一早,也不见叶寒、叶峭兄妹二人归来。
事已至此,元宝也只得当下随缘了。
临行之时,还是跟店家留下话:若是他们二人寻到这里,便告诉自己和巴图鲁的去处。
两人又带了些干粮,策马直奔吉林将军衙署而去。
晌午时分,二人抵达了目的地。
恒秀的表现有点出乎巴图鲁意料。
按理说,自己奉了乾隆帝的手谕,在某种意义而言,是皇帝的代言人,哪一方封疆大吏不得巴结奉承,给尽面子,可眼前这位吉林将军恒秀,从始至终都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热情。
后来巴图鲁才知道,这还是小事,让自己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。
恒秀看完乾隆的手谕,先是恭敬地轻轻放在桌上,面带愁容地说:“皇上的话恒秀自当照办,可眼下,衙门府库空虚,这许多银两,实在是拿不出啊。”
乾隆的手谕很简单,就是让恒秀办妥两件事:一是出钱;二是出地。
创建寺院,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件事。
在吉林地界上,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,自然非最大的长官恒秀莫属。
巴图鲁见恒秀这么说,心中未免不快:“偌大的将军府,怎么会连5万两都拿不出?”
“巴侍卫可能还不知道吧。”恒秀依旧是一副不急不缓的样子,“前些日子天降大火,焚毁我民居数千间,大半个吉林城满目疮痍,数万灾民惨状空前,府库银两用于赈灾尚且不足,又如何能拿出款项兴建寺院?”
“还有。”恒秀又顿了顿,“这建寺的地,倒是问题不大,但得需要跟辅国公知会一下,此地毕竟是他的封地嘛。”
巴图鲁跟元宝对视了一眼,又望了望乾隆的手谕,复对恒秀说:“可皇上的谕旨已下,将军总不要为难我一个小小的侍卫吧。”
巴图鲁在说“小小的侍卫”这几个字的时候,故意加重了语气。
首先,因为他并不小。
从官级来说,是正四品的“京官”。
恒秀虽为正一品,但毕竟是地方官员。
其中的微妙不说已明。
更主要的是这句话可谓绵里藏针,其潜台词是:“乾隆皇帝的谕旨已下,你纵使有千万个理由,总不会一分钱都不吐吧?若当真如此,你不是不给我巴图鲁面子,而是不给当今皇上面子。”